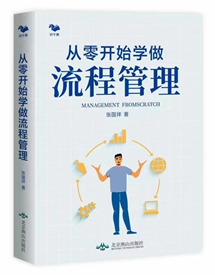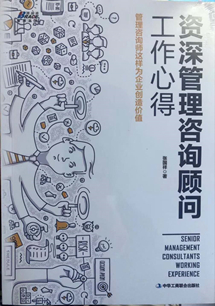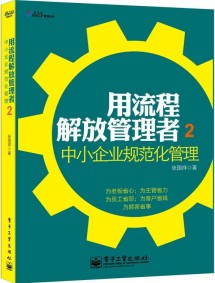关于父亲的记忆——祝天下父亲快乐
作者:张国祥
今天是周六,工作进展顺利,晚上给自己放了假,到街上转了一圈,发现商家的横幅都打出庆祝父亲节的字样。我知道父亲节也就这二年的事。具体哪一天为父亲节,从何而来,我还真不知道。
不过,到了父亲节,我还是会想起父亲。我有两个父亲:生父和继父。
生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角钱。继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二元钱。
生父因为身体有病,在我的记忆中,他没有正常参加农村劳动,都是在家养病。当然他也没有完全闲着。他去钓鱼、网鱼,或是自制土炸弹,去炸兔子、獾子,或下笼子套黄鼠狼。在家也种植果树,如桃、李、柿、枣、葡萄,他还裁种西瓜、香瓜和甘蔗。在他去世前,我家好像不愁菜吃,就是粮食不够吃。
这一角钱是怎么回事呢?就是种甘蔗。甘蔗一角钱一根,但在村里是卖不出去的,必须拉到十里之外的蒋湖农场去卖。平时没有人买,只有到了春节前才能去卖。父亲身体不好,通常由我和母亲拉过去。工具就是由父亲自制的独轮手推车。每车通常可拉三十根左右,百来斤重。一车卖完,充其量三元钱。但一般是不能凑整的。一是有小孩子来卖,只有八分、九分钱,母亲也会卖给人家一根;二是碰到熟人,母亲按亲疏关系也会送人家一根半根。一天能卖二块五,就是很好的收成。
那时正兴起割除资本主义尾巴运动,父亲不参加劳动,却在自家自留地种经济作物,受到了村里的批判。大批判的专栏里画了一幅砍伐甘蔗的漫画,下面写着:“干资本主义有力,搞社会主义有病。”虽然没有点名,可同学们看了都知道指的是我父亲。父亲的身体不能参加集体劳动,在家又不能侍弄自留地,父亲无事可做,病却更重了,吐血更加频繁起来。父亲得的是肺结核。我正读小学三年级,也开始学写文章。文章多是批判文章,正是批判前国家主席“三自一包”热火朝天的时候。那时候的批判文章千篇一律的结尾:“打倒XXX,再踏上一只脚,让他遗臭万年,永世不得翻身。”父亲看了我的文章,只说了一句话:“你看他臭不臭一万年?!”这是我父亲唯一一次评论我的作业。半年之后,我父亲就因病辞世,享年三十九岁。那天我还差十二天满九岁。
想到我的父亲,我就想到甘蔗一角钱,想到那评论作文的唯一一句话,还有那一个轮的车。我曾得过一场病,就是左膝生疮,手术之后,一个多月不能走路,每天上学,就是张法武、张法文俩兄弟用独轮车拉我上学,当然放学则有不少同学自发地送我回来。所以,从小至今,我对同学总是一往情深。
两年后,继父来到我们家,我读小学五年级。也是春节前,一个寒冷的冬天,我和继父去蒋湖农场买年货。春节期间,到底不同往常,我们要在柜台前等候。不知等了多长时间,前面没有顾客了,我往前挪了二步,却意外地发现柜台上有二元钱。我拿到钱,小声告诉继父:“爸爸,我捡到二元钱。”生怕别人听到。那知,继父接过钱,就大声对营业员说:“谁掉了二元钱,我小家伙(老家代指儿子)捡到了,先放在你这里,有人来找,就麻烦你给人家。”营业员接过钱,往货架上面一扔,就忙自己的去了,没有任何表示。我对继父的举动表示不解。
回家的路上,我对继父说:“万一别人找上来,营业员不承认怎么办?”继父说:“我们也不能在哪儿等别人。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放在自己荷包就行了。丢了的人找不到,也让他长个教训。”
第二年夏天,学校成立篮球队,为了参加公社比赛,老师要求我们队员自己买背心,学校统一印字。我找继父要二元钱,告诉他要参加公社的比赛,继父说没有钱。继父是有工作单位的,每月都有二十几元的工资。他不给,我就哭了。我想要是我的父亲,卖甘蔗也会给我买背心吧。我没有说话,只是很伤心地哭。继父没有办法,只好给了我二元钱。我当队长的篮球队在这次比赛中得了冠军。
我对继父这迟给的二元钱一直耿耿于怀,只是在我参加工作以后,每月都要靠借钱过日子(帮家里还债、借钱买砖建房,我对初工作单位的同事也是念念不忘),才对父亲的做法感到释然。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!
继父临近七十去世的,想到他,我常常想到这两次的二元钱。
我做父亲也有二十几年了,只是一个女儿的父亲。我深感“儿多母苦”,也恰好赶上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,我没有超生,也不想超生。对女儿花钱的要求,我几乎从未拒绝。如果我有几个孩子,对工薪层的我来说,能满足孩子的用钱要求吗?我感到很难。
想想我们的父辈,他们当时该有多难!